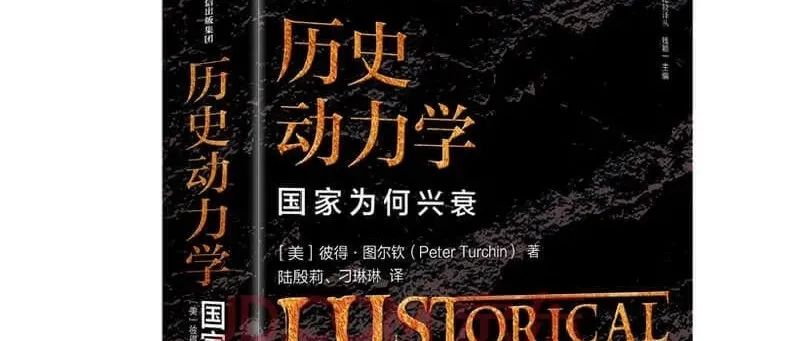
作者:劳拉·斯宾纳(Laura Spinney),出生于英国,曾居住在法国和瑞士。作为一名科学记者,她的作品已发表于《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自然》(Nature)、《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等刊物。此外,她还著有两部小说:《医生》(The Doctor)和《痛点》(The Quick)。其《苍白的骑士: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了世界》 (Pale Rider: 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一书2021年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文末有该书简介。
计算过去的模式和周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但它能帮助我们预防迫在眉睫的危机吗?
科学杂志《自然》在其2010年第一期中展望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年进展。到2020年,连接到互联网的实验设备将通过直接监测我们的大脑信号来推断我们的搜索查询。农作物将在三小时内将其生物量增加一倍。人类将顺利地结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几周后,同一杂志上的一封信给这个光明的未来投下了阴影。它警告说,所有这些进步都可能因日益严重的政治不稳定而脱轨,这种不稳定将在2020年左右在美国和西欧达到顶峰。信中解释说,人类社会经历了可预测的增长期,在此期间,人口增加,繁荣上升。然后是同样可预测的衰退期。这些 “世俗周期 (Secular Cycles)”持续两三个世纪,并在广泛的动荡中达到高潮–从工人起义到革命。
信中说,近几十年来,一些令人担忧的社会指标–如财富不平等和公共债务–在西方国家开始攀升,表明这些社会正在接近一个动荡时期。作者继续预测,2020年美国的动荡将没有美国内战那么严重,但比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暴力更糟糕,当时谋杀率激增,民权和反越战抗议活动加剧,国内恐怖分子在全国各地进行了数千次爆炸。
这个严酷警告的作者不是历史学家,而是生物学家。在他职业生涯的前几十年里,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用复杂的数学方法来说明捕食者和猎物的相互作用如何在野生动物种群中产生振荡。他曾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在其领域内受到尊重,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他已经解决了所有他感兴趣的生态问题。他发现自己被历史所吸引:人类社会的兴衰是否也能被少数变量和一些微分方程所捕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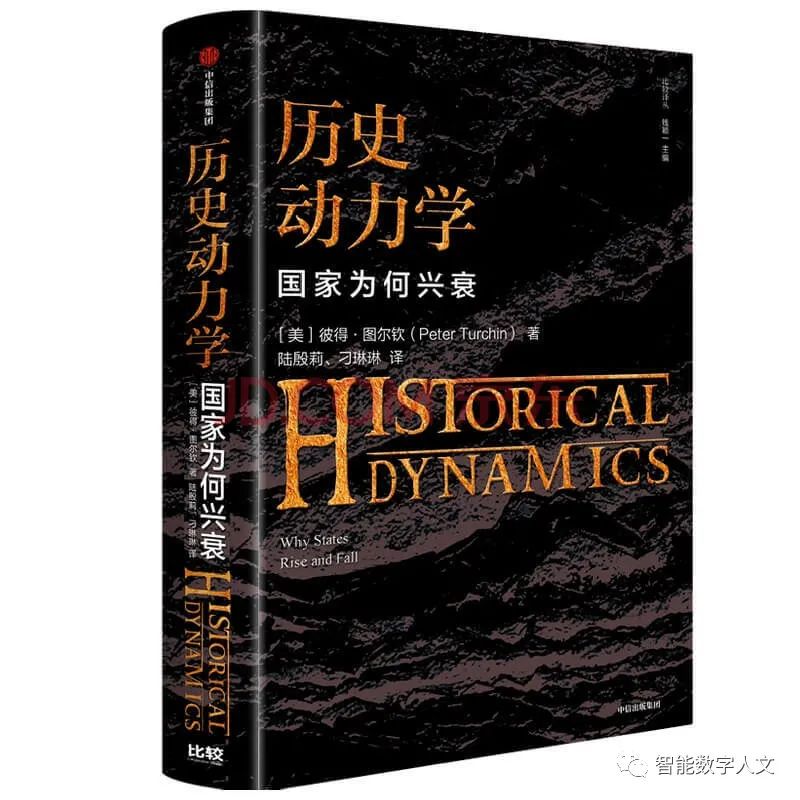
图尔钦着手研究历史是否像物理学一样,遵循某些规律。2003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历史动力学》(Historical Dynamics)的书,其中他找出了法国和俄罗斯从其起源到18世纪末的世俗周期。同年,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称为Cliodynamics,旨在发现这些历史模式的根本原因,并利用数学对其进行建模,就像人们可能对地球气候的变化进行建模一样。七年后,他创办了该领域的第一本官方期刊,并共同创建了一个历史和考古信息数据库,该数据库现在包含450多个历史社会的数据。该数据库可用于比较跨越大段时间和空间的社会,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政治不稳定作出预测。2017年,图尔钦成立了一个由历史学家、符号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人组成的工作组,以帮助根据历史证据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
图尔钦的历史研究方法,即利用软件在大量历史数据中寻找模式,直到最近才成为可能,这得益于廉价计算能力的增长和大型历史数据集的发展。这种 “大数据 “方法现在在历史学科中变得越来越流行。华盛顿州立大学的考古学家蒂姆-科勒(Tim Kohler)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他所在领域的 “辉煌时代”,因为学者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轻松方式汇集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从中提取真正的知识。图尔钦认为,在未来,历史理论将对照大型数据库进行测试,而不符合的理论–其中许多是长期以来的夙愿–将被摒弃。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将趋向于接近客观真理的东西。
对某些人来说,图尔钦2010年在《自然》杂志上所作的预测现在看来非常有预见性。如果没有任何最后一刻的意外,到2020年解码你脑电波的搜索引擎将不存在。在三小时内生物量翻倍的作物或主要由可再生能源供应的能源预算也不会存在。但是,美国或英国的政治秩序即将发生的动荡似乎越来越有可能。由美国非营利组织 “和平基金 “计算的 “脆弱国家指数 “显示,这两个国家的不稳定趋势在不断恶化,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则在稳步改善。
伦敦经济学院研究政治冲突的乔治-劳森说:”我们处于一个相当动荡的时代,只有伟大的大西洋革命时代可以与之媲美。”他指的是从1770年代到1870年代的时期,当时暴力起义推翻了从法国到新世界的君主。
Turchin认为他对2020年的预测不仅仅是对一个有争议的理论的测试。它也可能是未来事物的一种尝试:在这个世界上,学者们为未来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发出了相当于极端天气的警告–以及关于如何在其中生存的建议。
对于大多数研究过去的学者来说,解释为什么某事曾经发生与预测它将如何和何时再次发生是非常不同的。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Timur Kuran说:”我们不能生产规律。”
这种观点受到数学家和生物学家(如图尔钦)的挑战,并非偶然。他们的学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复杂性科学,它告诉我们,即使只是由几个运动部件组成的系统,也会因为这些部件的不同互动方式而产生复杂的行为模式。例如,太阳、地球表面和地球的大气层相互作用产生天气。这些相互作用可以用数学的方式来捕捉,用方程组或规律来预测系统在不同条件下的行为。这基本上就是天气预报的作用。
复杂性科学起源于物理学,研究基本粒子的行为,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它慢慢蔓延到其他学科。迟至20世纪50年代,很少有细胞生物学家会承认细胞分裂可以用数学来描述;他们认为它是随机的。现在他们认为这一事实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细胞分裂数学模型已经导致了更好的癌症治疗。在生态学中,人们也接受自然界中存在着可以用数学描述的模式。旅鼠不会像沃尔特-迪斯尼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大规模自杀,但它们确实经历了可预测的四年繁荣和萧条周期,这是由它们与捕食者的相互作用驱动的,也可能是与它们自己的食物供应有关。200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宣称,找到历史规律也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这不会发生,除非所有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人意识到,他们专业的工作模式,虽然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盖尔-曼说:”我们忽视了对整体进行粗略观察这一关键的补充学科。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用数学方法处理历史是有问题的。他们倾向于认为,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但只是非常有限的方式–例如,北爱尔兰的动乱历史可能对那里目前的紧张局势有所启示。如今,很少有历史学家寻找适用于跨世纪和跨社会的一般规律,或者可以用来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预测未来。这是19世纪科学史学家的目标,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发,而这种方法现在被认为有很大的缺陷,并与帝国的叙述有着致命的联系。
德克萨斯州南卫理公会大学的历史学家古尔迪(Jo Guldi)说:”我们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科学家群体,已经投入了60年的共同努力,以剥离那些叙述中包含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以及一般的欧洲中心主义。”他补充说,历史学家们担心数学方法会拖累他们倒退。科学和人文之间也存在着古老的不信任。当古尔迪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2014年出版的《历史宣言》一书中呼吁他们的学科拥抱大数据,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过去时,他们在该领域的美国权威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上受到了抨击。古尔迪说:”这可能是过去30年中最血腥的攻击之一。”不仅在历史学家中,而且在许多普通人中,都有一种直观的感觉,即人类不能被简化为数据点和方程式。方程怎么能预测圣女贞德,或奥利弗-克伦威尔?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Diarmaid MacCulloch说:”历史不是一门科学,它的底部是人类的行为,而这是可怕的不可预测的。”
“这种说法完全搞错了,”图尔钦认为,他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康涅狄格大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系的教授,现在也隶属于维也纳的复杂性科学中心。”正是因为社会系统如此复杂,我们才需要数学模型。” 重要的是,由此产生的规律是概率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这意味着它们容纳了机会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空洞的:如果天气预报告诉你有80%的机会下雨,你就会带上你的雨伞。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文化进化的著名学者彼得-里奇森(Peter J Richerson)说,像世俗周期这样的历史模式确实存在,而图尔钦对它们有 “唯一合理的因果解释”。(里奇森指出,这也是目前唯一的这种说法;这个领域还很年轻,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论出现。)
其他历史学家认为,图尔钦的工作–不仅包括历史和数学,还包括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和环境科学家的研究–为这些学科内几十年的专业化提供了亟需的纠正。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加里-费恩曼(Gary Feinman)在2016年与图尔钦及其同事的研讨会后写道:”我们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迫切需要这种总体的、合作的、比较的努力。”不过,其他人对以复杂生物系统的方式研究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新见解感到兴奋。一些硅谷高管也对图尔钦的预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图尔钦说:”他们明白了,但随后他们有两个问题:他们如何才能从这种情况中赚钱?以及他们应该何时在新西兰购买他们的地块?”
当图尔钦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寻找历史的数学描述时,他发现另一位学者在20年前就为他奠定了大部分基础。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是一位由数学家转行的历史学家,作为哈佛大学的学生,他曾经用数学来编纂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民主思想。”他最近告诉我:”我试图把托克维尔的论点编制成一组方程式。”我得到的结果并不好。” 戈德斯通后来成为第一个将复杂性科学应用于人类历史的人,并得出结论,政治不稳定是周期性的。其结果是对革命进行了数学描述–这是图尔钦继续完成的社会变革模型的一半。
在戈德斯通开始研究的时候,也就是70年代中期,对革命的普遍看法是最好理解为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但戈德斯通提出了两个不符合这一观点的观察。首先,来自同一阶级,甚至同一家庭的人,最终往往会站在对立面作战。其次,革命集中在某些历史时期–14和17世纪,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但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为什么阶级矛盾会在这些时期而不是在其他时期爆发。他怀疑有更深层次的力量在起作用,他想知道它们是什么。
偶然的是,由于他缺乏资金,戈德斯通最终成为哈佛大学人口学家乔治-马斯尼克(George Masnick)的助教,后者向他展示了二战后美国婴儿潮的深刻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那次青年潮伴随着社会中新的紧张局势,包括对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和对激进意识形态的渴望。戈德斯通想知道,像这样的繁荣是否会促成其他社会的动荡时期,在80年代,他开始梳理档案,了解欧洲革命前几十年的人口增长情况。
仅仅在几年前,他所需要的详细程度是无法得到的,但英国的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史小组,以及欧洲各地的类似小组,已经开始根据教区记录等资料重构人口历史。1978年出版的科林-麦克维迪(Colin McEvedy)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的《世界人口历史地图集》(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也使戈德斯通受到鼓舞,他们在其中强调了几千年来欧亚大陆人口繁荣和衰退的 “惊人的同步性”。在进行数字计算的几个月后,他迎来了他的曙光时刻:”这是令人震惊的:在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革命或叛乱之前,确实有三代人的人口增长。”
在18世纪,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牧师认为,人口最终会超过其资源,在冲突和疾病的毒云中内爆,直到再次减少到可管理的比例,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戈德斯通继续构建的理论借鉴了马尔萨斯的观点,但重要的是,它消除了这种循环的令人沮丧的必然性。它声称,人口增长给社会带来了压力,而社会又以复杂和独特的方式引导这种压力。他使用地震做类比:地震力在高原下积累,直到它开始摇晃,但高原上的建筑物是否站立、倒下或遭受某种中间程度的损害,取决于它们的建造方式。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会在历史上聚集,但在特定的动荡时期,并非所有社会都会屈服。
戈德斯通认识到,一个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国家、精英、群众–会对压力做出不同的反应,但他们也会相互影响。换句话说,他所处理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行为最好用数学方法来体现。他关于革命发生原因的模型由一组方程式组成,但粗略的口头描述是这样的:随着人口的增长,会有一个点,它超过了土地的支持能力。群众的生活水平下降,增加了他们进行暴力动员的可能性。国家试图抵制这种情况–例如,通过设定租金上限–但这种措施会疏远精英阶层,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由于精英阶层也一直在扩大,并为有限的高地位工作和装饰品进行更激烈的竞争,整个阶层不太愿意接受进一步的损失。因此,国家必须动用自己的国库来镇压群众,从而推高国家债务。债务越多,它应对进一步压力的灵活性就越小。最终,被边缘化的精英成员与群众站在一起反对国家,暴力事件爆发,而政府却无力遏制。
戈德斯通提出了衡量群众动员潜力、精英竞争和国家偿付能力的方法,并定义了他称之为政治压力指标(psi或Ψ)的东西,它是这三者的产物。他表明,Ψ在法国大革命、英国内战和其他两个17世纪的主要冲突–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危机和中国的明清过渡时期–之前就已飙升。然而,在每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个因素在其中:机会。在其他情况下,一些微小的破裂–比如收获失败,或者外国侵略–可能很容易被吸收,在不断上升的背景下Ψ导致冲突爆发。虽然你无法预测触发因素–也就是说,你无法准确知道危机何时发生–但你可以衡量结构性压力,从而衡量这种危机的风险。
这是一个简单的模型,戈德斯通也承认这一点。虽然他可以证明高Ψ可以预测历史上的革命,但他没有办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取决于Ψ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精确组合,以及它们与特定社会机构的互动方式。尽管不完整,但他的努力使他从一个令人沮丧的新角度来看待革命:不是对僵硬和腐败的旧制度的民主纠正,而是对生态危机的反应,即社会无法吸收快速的人口增长,但很少能够解决这一危机。
这些模式也不局限于过去。当戈德斯通为他的巨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叛乱》(Early Modern World)做最后的润色时,苏联正在解体。他指出,在1989年之前的20年里,Ψ在整个苏联集团中急剧上升,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持续走高。他还写道:”令人惊讶的是,今天的美国在国家财政和精英的态度方面,正沿着导致早期现代国家走向危机的道路前进。”
当戈德斯通的书在1991年问世时,历史学家们对其进行了抨击。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纽约书评》中写道,戈德斯通的工作 “在构建一个叫做政治压力指标的东西方面过于大胆和模糊,而这个指标就像独角兽一样真实”。戈德斯通承认,这本书并没有产生他所希望的影响。”他回忆说:”这本书和我都有点落入俗套。然后在1997年的某一天,他接到了彼得-图尔钦的电话。
当时,图尔钦正在经历他戏称的 “中年危机”–40岁时,他放弃了生物学,和历史一起跑了。吸引他研究社会内爆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他曾亲身见证了一个社会的自我毁灭。他出生在俄罗斯,但他的家人在1978年叛逃到美国,而他直到1992年才回到莫斯科。”他回忆说:”那一年,事情完全崩溃了。那是12月,黑暗,可怕。到处都是喝醉的人。” 他和妻子在去市场的路上经过一辆被炸毁的汽车,看到黑手党从惊恐的摊主那里勒索现金,而警察则在一旁观看。这些画面一直伴随着他。
当图尔钦看到戈德斯通的书时,他发现它 “非常了不起”,他说。但该模型并不完整。”他描述了社会如何陷入危机,而不是如何摆脱危机。所以图尔钦决定完成这个模型,并找出它是否适用于更大范围的时间和空间的人类社会。戈德斯通专注于早期现代时期–大约是从1500年开始的四个世纪;图尔钦将把研究的起始日期推到近8000年前,即新石器时代。这意味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在这一点上他是幸运的:从1970年代对那些教区登记册的借鉴开始的历史的量化转向,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更是不断加速。
虽然历史记录仍然是零散的,不完整的,但现在它们有可能讲述一些关于过去的人们如何生活的新东西,即使没有他们的书面痕迹–而且更好的是,从数学家的角度来看,可以把数字放在他们身上。例如,格陵兰岛的冰芯被证明是欧洲经济活动的一个精致的替代物,因为永久冻土捕获了污染并跟踪其数个世纪的波动。贵族别墅的规模和建筑说明了精英的竞争,硬币的囤积说明了对迫在眉睫的纷争的焦虑,而骨骼的畸形显示了营养不良–能够代表生活水平。这些代用指标的信息价值早已得到认可,但现在有了关于它们的量化数据,时间跨度达数十年,有时甚至是数百年,这意味着你可以辨别出不同时期的趋势。对于一个特定的变量,你拥有的代理变量越多,你就能更准确地描绘出过去的情况。
在2003年的《历史动力学》中,图尔钦证明了从公元前一千年到大约1800年期间演变成现代法国和俄罗斯的社会的世俗周期模式。他还表明,这些社会的稳定性存在较短的振荡,持续时间约为50年,他称之为 “父子循环”:感知到社会的不公正,一代人开始用暴力来纠正它,下一代人在暴力的后果中成长起来后,对暴力有所收敛,第三代人重新开始。
许多学者对图尔钦的怀疑程度不亚于十几年前对戈德斯通的怀疑。犹他州立大学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在《自然》杂志上写道:”严肃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对周期性理论不屑一顾。” 但是图尔钦才刚刚开始。2010年,他和牛津大学的两位人类学家推出了Seshat,这是一个以古埃及记录女神命名的历史和考古信息数据库,以更好地组织这些数据,支持不同社会的比较。
Seshat受到了对大数据更普遍的那种批评。批评者说,仅仅因为有大量的数据,并不意味着数据更可靠。相反,这样的数据库有可能放大那些最初记录信息的人的解释偏见,同时剥离其背景。Seshat的创始人反驳说,偏见是历史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有对大量数据的分析才能使一个信号–接近真相的东西–从噪音中脱离出来。
迄今为止,Seshat的创始人和他们的90多位 专家合作者–包括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收集了从安第斯山脉低地到柬埔寨盆地、从冰岛到上埃及等社会的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图尔钦表明,同样的两个互动周期–世俗的和父子的–适合整个欧洲和亚洲的不稳定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批农民。在古埃及、中国和罗马–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前工业社会中,它们都存在。
下一个问题很明显:这些周期是否也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起作用?图尔钦更新了Ψ,以反映形成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力量,并选择了适合工业化世界的新代用指标。其中包括代表大众动员潜力的实际工资;代表精英竞争的参议院 filibustering rates和耶鲁大学的学费;以及代表国家偿付能力的利率。然后,他计算了美国从1780年到现在的Ψ。它在1820年左右所谓的好心情时代是低的,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前后–是高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又是低的。自1970年以来,它一直在稳步上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注定要面对危机。许多社会已经避免了灾难–而图尔钦正在建立一个模型,以找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在20世纪80年代末,图尔钦曾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森林,那里的木材工业资助他研究一种叫做南方松树甲虫的害虫的周期性和昂贵的侵扰。当时,控制甲虫的标准程序是在虫害发生地喷洒杀虫剂。特钦表明,这只是推迟了虫害,因为它杀死了另一种甲虫,而这种甲虫是害虫的天敌。一个更好的策略是砍伐和清除受影响的树木。更广泛地说,他表明有可能对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进行干预,使其危机不那么严重,并使其恢复的机会最大化。
图尔钦希望能发现类似的策略来缓解人类社会的危机。如果他和戈德斯通对历史建模所采取的方法是正确的,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可以有意义地询问2020年为我们准备了什么,而且还可以询问几个世纪以来的未来是什么。我们不应该指望从这门新的历史科学中得到任何预言,但它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对我们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威胁,并采取行动来减轻它们。
虽然社会倾向于通过戈德斯通描绘的路径进入危机,但图尔钦发现,他们通过一系列可能的轨迹离开危机,从快速恢复到完全崩溃。这是因为危机使一个社会对外部扰动非常敏感。如果没有其他破坏稳定的事情发生,它可以恢复–就像英国在1688年几乎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之后所做的那样。但是,一个小小的额外冲击就会把它推向更坏的结果,甚至是崩溃。苏联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之前就已经衰落了,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其衰落归咎于该事件时,可能并不完全错误。
为了更好地理解周期的这一阶段,图尔钦和其他人计划建立由数千或数百万人组成的计算机模拟社会–所谓的基于代理的模型–并根据他们从真实社会中推导出的规律对它们进行编程。他们可以让这些模拟社会承受压力,例如通过注入虚拟的青年暴增,并观察对国家、精英和大众的下游影响。一旦Ψ达到危险的高水平,他们可以增加一个冲击–比如说,以外国入侵的形式–或者通过加强社会的基础设施来增加复原力,并观察它的反应。他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要怎样才能使一个处于危机中的社会走向完全崩溃?哪些干预措施会使它转向一个不那么血腥的结果?为什么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有弹性?
当然,我们在气候危机方面的经验表明,即使我们能够像预测天气那样预测未来,并提出一套预防措施来避免社会崩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能够凝聚政治意愿,就这些建议采取行动。虽然人类社会在灾后重建方面的能力确实远胜于一开始的预防,但也有例外。图尔钦指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新政,他认为当时美国的精英们同意更公平地分享他们不断增长的财富,以换取 “政治经济体系的基本要素不会受到挑战 “的隐性协议。图尔钦认为,这个协议使美国社会能够退出一个潜在的革命局面。
戈德斯通继续传播这样的信息:这种契约可以再次发挥作用。现在,他是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的公共政策教授,为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长期战略的美国情报机构–提供咨询,但他说他的想法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影响。去年4月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社会崩溃问题研讨会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历史上的社会经常在危机迫近的迹象无法忽视的情况下也不采取行动。他认为这是因为精英们在事情开始分崩离析后的一段时间里继续过着高尚的生活,他们的财富和特权使他们免受动荡的影响。
图尔钦认为,历史学家将很快接受复杂性科学,就像生物学家在半个世纪前所做的那样。他们将意识到,这使他们能够看得更深更远,辨别出人眼不可见的模式。事实上,这已经在发生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机构已经成立,如剑桥大学的存在性风险研究中心,其目标是鼓励决策者思考历史的长期教训。参加普林斯顿会议的是美国陆军工程研究与发展中心聘用的风险分析师,他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参考过去的经验使美国对未来的威胁有更强的抵抗力。
在图尔钦看来,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发展,但2020年快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法律制定机构现在都因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分裂,几乎无法运作。在这两个国家,心怀不满的精英成员以人民的名义夺取了权力,却没有解决造成这种萎靡的根本原因:日益扩大的不平等、膨胀的精英阶层、脆弱的国家。
戈德斯通提供了他所能提供的安慰。他说:”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人能够想象到欧洲在20世纪60年代会变得多么富有,或者整个欧洲大陆会变得统一。尽管事情可能在十年或二十年内变得很糟糕,但一旦你度过危机,它们很可能会好得多。” 这是历史周期性观点中固有的安慰:每一次下跌之后都有另一次上涨,正如每一次上涨之后都有另一次下跌。对我们这些仍然在世的人来说,事情会再次好起来。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智能数字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