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与主体性: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
文 /刘超
随着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媒体已牢牢占据人类知识传递结构的轴心位置。数字科技统摄了人类社会领域,支配了人类的思维和实践。数字所支撑的计算思维造成了数字化治理和数字化生存,各行各业都呈现出新业态。“风险社会”日益复杂化,形成了一系列奇异的文化景观和知识生态。
从数到术:数字统治下的知识情境
数字简约、抽象而纯粹,是数学和科学体系的基石,如双刃剑般扎入人类社会。数字技术的大规模运用,让人类遭遇“信息乌托邦”,受困于“信息茧房”。有人把算法理论看成是西方工具理性的基石。马文·明斯基认为:“计算机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工具,算法已成为一种文化崇拜,其核心就是按设定程序运行以期获得理想结果的一套指令。”莱布尼茨指出,认知思维和逻辑可被简化为二进制表达式。他认为逻辑总能被无情地简化,于是将所有逻辑思维简化为机械运算,用一系列简单的二元区表示复杂难题,从而构建了最简单的语言片段与复杂的人类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的确彰显了巨大威力。就此而言,数即是术,极具工具性和宰制性。数字技术带来了新的治理术,重塑了新的社会秩序和知识体系,改变了人类思维和生存环境。这一改变的烈度、深度和广度异常罕见。把计算思维移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工程领域,必将数字的特质导入知识建构和社会治理中,这意味着极大冒险。

物极必反,当“人类对工具的依赖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副作用加之于身”。尼尔·波斯曼认为,在信息化时代,技术垄断文化,文明向技术投降,而数字科技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软”技术仍有其阴暗面,容易伤害文明。在大数据“投喂”之下,算法持续智能化,人类的能力被空前放大。许多技术专家放言“数据决定成败,算法成就未来”“未来属于算法和它们的缔造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则表示:“我们塑造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我们。”的确,“一种技术塑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工具“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思维和世界观”,人最后“难以避免地被他每天抡起的那柄锤子所‘锤化’” 。
如今,人类已然进入数字时代,数字科技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知识生产、组织形态和社会治理,也改变了人际关系、人机关系。
知识裂变及自反性
在算法社会中,知识体系发生了深刻撕裂和变异,其内涵、形态与功能也发生蜕化。由数字为基础建构的科学文化和以经验语言所建构的人文文化,产生了深度分化,二者沿着各自路径演化。
近代以来,科技高歌猛进,对此的反思亦时有所见。1952年,哈耶克出版了《科学的反革命》,率先在西方掀起了对科学的反思。几年后,英国科学家、小说家 C. P. 斯诺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表示,西方社会知识人的生活被名义上分成两种文化,分别聚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者严重撕裂,阻碍了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两者亟需合作。这一命题提出后,随即在多国引发反响。科技专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在知识结构、价值立场、思维方式等方面往往大相径庭,因此有着迥异的世界图景。任何研究几乎都意在寻求某种相对确定的关联性,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于此有着巨大分野:前者倾向于将任何联系化约为一定的数量关系;后者则指向某种有机联系;前者强调工具理性,后者强调价值理性;前者更具刚性、宰制性,后者富有柔性、对话性,蕴含着生命质感、关切社会痛痒。二者构成相制衡的力量极。19世纪以来,整个知识领域经历了科学化浪潮,“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人文知识则被挤兑至知识领地的边缘。

哈耶克
在数字的影响下,学科演变加剧,由此出现了知识分化及钝化。数字科技的强势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其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剧了两种文化的裂变与整合。数据科学野蛮生长,深度渗透至人文社会科学中,“学科殖民”日渐明显。卡尔·波普尔指出,科学家“能够立即进入问题的核心……进入一个有组织的结构的核心”;哲学则发现自己“面前没有一个有组织的结构,而是一堆废墟似的东西(虽然也许有珍宝埋于其下)”。吉登斯坦言:“正是自然科学的发现和发明,使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的社会科学,迄今为止产生的影响要逊色得多。”两种文化撕裂的同时,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鸿沟也在扩大。前者是技术垄断的工具和坚定同盟,乘着科学的东风而兴盛;后者则仅剩人文科学独力苦撑,因为社会科学经过长期的科学化的侵染,本身已成为“大科学”的一部分,已适应当今的学术范式和评价体系。人文科学则因其默会性、反思性和不确定性,因其隐喻、转喻、象征等修辞的“硬核”,承受住了工具理性的侵蚀和科学化的冲刷。然而,正因如此,使其在科学思维主导的学术体制中日渐边缘。总体上,知识体制的批判性思考已日益稀缺,我们往往沉迷于专业议题的丛林中,越来越少地介入公共议题。
由于资本等的侵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种坚实、稳固的东西遂愈显珍贵。为了应对不断来袭的风险和流动的现代性,人们加强了控制,最大限度地刻意追求确定性知识。然则求而不得,追求力度的提升造成变化加快、流动性增强,反而愈发远离了确定性,使其更显匮乏。每一次知识创新,都酿生着知识毁灭,强化了知识的自反性。
多重夹缝中的知识人
现代科技以其强大的手段构建了一个虚拟世界,用海量信息支配了人类的时间、注意力乃至思维方式,从而剥离了人与现实世界及意义世界间的有机联系,加剧了人类精神世界的贫乏和凋敝。其表现包括:
第一,现实感缺失。算法操控信息供给,造成虚拟世界或“信息茧房”,容易让人生成虚假意识。久之,易使人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能力蜕化。每个鲜活的生命都需要与真实世界建立稳固的联结,需要在物质性实践中融入世界,唯此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与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以各自方式与大地相连。而技术则使这种现实感日渐淡薄。人与真实世界的联结日渐脆弱。人游离于现实之外,事物的意义就会飘散,必须植根现实,才能获得深刻的现实感。
第二,虚化及无意义化。消费社会不断撩拨人的欲望,人被简化为对“娱乐的探索”。技术的蔓延又使人由主体变成工具人,成为达成数字目标的手段。以数字为基石、以递归为逻辑构筑的科学文化,呈现的是计算思维构建的一套纯粹理性。在数字化的洪流中,个体如无根的浮萍,难以扎根大地。人是需要意义的动物,无意义的人生,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经过数字化的处理,人只剩理性的算计,其主体性内涵中难以量化的向度都被无情地抑制和摒弃了。主体性消解及意义感的蜕化,使人日趋空虚、压抑,成为空心人。学术“真正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心灵”。而在数字中,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消隐、消解了。意义的凝定需要特定载体,而在流动的现代性之下,意义无法寻得坚实的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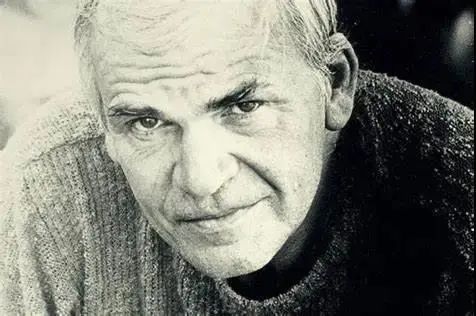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作者米兰·昆德拉
第三,单维化、同质化及去个性化。世上“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种想法”。人绝非若干冷冰冰的数据所能涵盖,然而在数字抽象之后,人无差别地成为一系列数据的载体。人具有无限的丰富性,正是人的丰富性,成就了世界的丰富性和无限可能性,这对知识生态的活力和健全是至关重要的。个性是人存在和发展之基,是社会活力和弹性的保障,参差百态乃是幸福之源。而科技滥用极大地强化着人的单一化、同质化甚至极化,这无疑隐含着不可预知、不可控的巨大风险。
第四,结构失衡。人不是纯理性的算计机器,而是理性与非理性竞合的主体。非理性因素如欲望、直觉、想象等,是人类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极,是对理性因素的平衡器,也是激发人类活力、知识创新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在根本上保障着科技与人文、物性与人性的平衡。技术统治造成的种种失衡,打破了人精神结构的平衡,不仅制约了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也限制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无限可能性。
第五,透明化的侵扰。技术的高度进化和监管的加强,造成了“透明社会”或“无隐私社会”。在理性滥用和大数据的劲流中,人类生命的每个痕迹都清晰可见,已无“私”可“隐”。然而,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知识创造,终究还是需要一定的陌生化、神秘性。彼得·汉德克说:“我是凭借不为人所知的那部分自己而活着。”私人空间和神秘感的消失,不仅给人带来不便不适,也钳制了个体的活力、自主性和人类的想象力。越是高度创造性的精神劳作,越具有个性化和不确定性,也就越需要宽松的环境。历史上许多人物都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私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相对自主的空间,成就了他们非凡的才情和贡献。为追求可见、可控而强力实行过度管理、全景监测,会造成私人空间的缺失,将极大地抑制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 阻遏高水平的知识创造。
知识生产体制的数字化变异
在数字科技主导下,知识体系重新洗牌,加速学科分化、分类和分层,隐隐对知识进行了重新定位、定义和定价,深刻改变了知识生产体系。举其要者有:
第一,组织化与项目化。知识生产持续组织化,体制化程度日增,科层化随之增强。知识生产主要依赖专业机构的规模化运作,进一步巩固了大科学体制;而体制外或个体化知识生产持续式微。各巨型大学都内外矛盾重重,相关利益高度分化,而有效的治理结构能使之“更加成熟老练地对付矛盾”。面对复杂社会的“无物之阵”,个体如漂浮的原子,渺小而无力。此外,人们的研究越来越依赖项目,“项目化生存”成为常态。这对知识生产的个性化、自由度都产生了强力抑制。人被数字所支配,常常表现为被项目所规训。

第二,知识生产逻辑的变化。在计算思维影响下,效率至上的绩效主义、追求可控可监测的审计文化盛行。效率至上试图取代学术自主,审计文化试图挤压学术文化,量化管理持续升级,学术评价(排名)日渐沦为数目的盘点和比拼。管理主义、绩效主义和计算思维支配了知识生产。众多高校参照企业模式进行治理,至此,“学术资本主义”达至新形态。在此逻辑和生态之下,科研从探索未知的非功利实践,逐渐异化为追逐绩效的功利行为。数字化的思维和治理方式,源于对效率的极度追求,由此造成了自由与效率、个性与规制失衡。社会逻辑无保留地衍射到知识系统中,在此趋势下,“只见数字不见人”,人逐渐自我消解,消失于数字的丛林中,算法则大行其道。
第三,评价体系对知识的再“定价”。计算思维认为那些可见可比、可控可监测的知识最有价值,意即可量化程度(与数的关联度)决定知识的价值大小。这样一来,思辨传统和理论研究被明显边缘化。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人们优先追求的是确定性的知识,是可见可量化的知识和“硬科学”;高度依赖经验、意义、默会知识和不确定性的人文科学势必面临挑战,若不接受科学的规训,就只能出局。不同的院系、学科之间关系重组,计算(机)科学成为新宠。
第四,研究范式的变迁。数据科学持续发展,隐然成为“第四范式”,与之相关的学科也行情见涨。这加剧了两种文化的矛盾。科技的强势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其垄断地位。人文社科的研究日渐计量化,没有数据就没有发言权。这导致学科生态的变迁,也导致学科的变异。为规避风险和不确定性,许多研究已很少关涉思想、价值、意义等议题,渐失本应有的学术想象力和否思性。量化考核所向披靡。排名成为“紧箍咒”,令许多高校和学者被“困在系统里”。个性因此而消散,主体性因此而消隐,工具性日渐强大。
余 论
计算思维负载着科技、资本对人文的监控、物化和异化。技术变革进一步促成物性和人性的变化。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强,自反性剧增。整个知识系统的复杂性持续升级,知识不断裂变和重构。在数字时代,研究工作成为知识生产线上的学术工业。学术工业繁荣,知识生产效率猛增。它在撩拨和满足人类欲念的同时,也抑制了人类的自我,加剧人类的依赖性。人在自我追求的同时,孕育着自我消解和自我否弃,由此形成新的困境,即知识茧房。个体受困于知识生产系统,知识生产体系又受困于资本逻辑、绩效主义。由此,个体的主体性与知识生产体系的主体性都受到双重的深度抑制,极大地限制了知识的人本性和创造性。在算法中,人们暂时获得了虚拟的解放和自由的幻象,实则陷入了自我迷失,主体性被侵蚀和消解。就此而言,尽管知识是力量,但它有时带来的不是解放。
如今,两种文化严重失衡,亟需再平衡,以矫正知识生产逻辑的扭曲。我们需要用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用人的德性为科技立法,用人文的力量平衡冷峻的计算思维,用法律和制度来规束技术风险。知识生产中不仅需要物性的力量,也需要人性的光芒。在强调组织化知识生产的同时,不妨为个性化的知识创造保留一席之地;在彰显理性之威力的同时,不妨为灵性留些许空间。这些“无用”的东西,可以滋养人的情感和意义世界,很好地平衡人类的精神世界,组成一个完整和谐的世界。
转载授权&作者信息: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2021年4月23日发布的文章《刘超|数字化与主体性: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算法社会:智能传播时代的文化与走向”圆桌会议④》,已获授权。
原文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作者刘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编辑 | 李钶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数字人文资讯):学术前沿 | 数字化与主体性: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