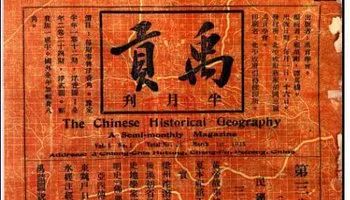作者简介:
黄义军,女,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博士。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出版专著《宋代青白瓷的历史地理研究》和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已出版学术译著3种,其中包括美国地图史学家马克·蒙莫尼尔著《会说谎的地图》(How to Lie with Maps);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地图学史》翻译工程”子课题“东亚和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地图学史”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地理和地图学史。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地理各主要分支的研究进展,学界已有相关综述。从2019年开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开辟“近7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专栏,对历史交通地理、古地图与地图学史、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疆域与政区变迁的成果进行了总结;《中国科学:地球科学》也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专题”栏目,第11期发表《近70年来中国自然地理与生存环境基础研究的重要进展与展望》《中国人文地理学70年创新发展与学术特色》。
本文通过检阅2015—2020年正式出版的论著及相关期刊论文,对近年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出现的新趋向进行总结,认为近年来传统学科分支呈现出细化和深入的趋向,多学科合作和数字人文持续发展,出现了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理、基层社会治理、边疆民族历史地理、地图学史等热点问题。
一、传统学科分支的细化与深入
尽管近年来历史地理各分支均取得了成绩,但限于篇幅,这里仅以表现突出的4个分支为代表,说明传统学科分支的细化与深入。其中,沿革地理学以考订疆域、政区、名胜等沿袭与变革为主要内容,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前身,也是历史地理各分支的基础,在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因此,这里将沿革地理单列成一类。
(一)沿革地理研究。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深化突出表现在采用多重性质的史料进行考证分析,特别是广泛采用新近发现的传世和考古发掘出土的新史料。此类研究不仅考证具体的地点、政区和疆域,还涉及一些重要的沿革地理问题。例如,由于历史文献的不足,西周早期封国的地望与范围存在不少谜团。武刚《周原出土昔鸡铜簋与西周韩国封建问题新证》(《历史地理》第38辑,2019年)根据2014年考古队在宝鸡市周原M11墓葬中发掘出土的昔鸡铜簋铭文,澄清了历史上对于韩国始封地的争议,证明西周时期的韩国先封于陕西韩城一带,后迁徙到河北地区,与燕为邻。先秦郡县制问题也有所推进,如王进锋《清华简〈越公其事〉与春秋时期越国的县制》(《历史地理》第38辑,2019年)通过对清华简简文《越公其事》的研究,发现设县也是春秋时期越国管理地方的重要手段。越国的县都设在边境地区,遣官管理具体的事务,越王对这些县具有很强的控制力。
沿革地理的研究,除了延续与16种正史地理志相关的考证之外,还对正史地理志载之不详或者存在错误的边疆民族地理等进行考订。从时段上看,呈现向近代和当代靠近的趋向。
(二)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历史政治地理仍然是重中之重。选题涉及国际、国内和地方三种尺度。就视角而言,既有断代政治地理研究,也有就某些政治地理要素展开的探讨。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对西方政治地理相关术语的讨论以往并不多见。边界是政治地理的重要概念,初冬梅《西方政治地理学对边界问题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梳理了西方政治地理学对边界问题的研究脉络,提出我国当前需要重视的边界研究议题。此文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古代疆界的具体形态与性质是近年提出的新话题。鲁西奇《封、疆、界:中国古代早期对于域界的表示》(《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对中国古代早期的封、疆、界进行了概念上的澄清。黄纯艳《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则指出,受其与对峙政权关系的影响,宋朝存在多种形态的疆界,划分疆界出于实用目的,核心是分隔版籍与非版籍的民和地,保护赋役来源与直辖郡县安全。
历史学界对“活的制度史”的强调,推动了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从文本考证向考察具体实施过程的转变,这就必然涉及制度在不同地域实施的差异性。例如,闫建飞《唐后期五代宋初知州制的实施过程》(《文史》2019年第1辑)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州郡分权出发,考察了从唐到宋,州郡长官由刺史向知州转变的过程,以及知州制实施的地域差异及其原因。
历史政治地理包括层级、幅员、边界、组织、等第诸要素,傅林祥《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范》(《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复原了清初江南、湖广、陕西三地省级官员衙门的分官设治及其行政体系调整的过程,揭示了清廷对于政治地理诸因素的慎重考量。
(三)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者分布于多个领域,因此其成果体现出多学科的视野。近年来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就时段而言,仍然集中在明清和近代;就内容而言,以单个城市居多。已有的研究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其一,时段的扩大,史前与近现代城市受到较多关注(详后);其二,有关城市选址与城墙修筑方面的个案研究增加了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视角(详后);其三,对都城的探讨呈现新意;其四,地方城市的研究在多个方面有所推进;其五,关注城市空间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其六,区域城市方面涌现新作。
都城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来的研究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出现了突破。宏观方面,如张学锋《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8期)对魏晋南北朝隋唐都城的形制特征进行总结,提出了一个有别于中国古代都城“多宫制”特征的“中世纪都城”概念。魏斌《南朝建康的东郊》(《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则对前人较少关注的都城郊区进行了探索,在考订复原的基础上,指出建康东郊的发展是都城内部权力向郊外“溢出”的结果。
地方城市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的推进主要体现在城市形态的演进及其思想性、城市管理等方面。城市形态方面,钟翀《上海老城厢平面格局的中尺度长期变迁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辑)从城市历史形态学中康泽恩学派的研究思路出发,重点考察中古以来上海城镇街道系统、建成区地块集聚形态的演化历程,对古代城市特征要素、长期变化规律与速率进行了思考。潘晟《宋代的常州——城市形态与科举的地理阐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4辑)则跳出城市形态研究的传统“实用”取向,揭示出思想资源和文化权力对城市形态的塑造过程。
城市管理方面,接续有关中古里坊制的讨论,出现了有关宋元明清时期城市管理的个案研究,如来亚文《宋元与明清时期嘉兴城中的“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辑)考证复原了明清时期嘉兴城的坊区,并由此上溯至宋元时代坊的形态,指出宋代嘉兴的城市管理存在附郭县管辖的乡、界、坊(巷)三级结构。
近年来城市空间所体现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变迁为更多的研究者所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以近代为主,也有少数文章涉及传统时期,如陈彩云《从国都到省城:元初对杭州政治空间的改造》(《历史研究》2020年第6期)考察了元军占领临安后对南宋都城政治空间的改造,将城市空间变化置于重大社会历史变迁的语境下加以探讨,是本文的一大新意。
区域城市方面,孙靖国《桑干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以城市的职能与选址机制为中心着眼点,对桑干河流域从秦汉到20世纪80年代的城址变迁与城市分布格局进行考察,并对影响区域城市分布、选址的各因素作了分析。
(四)地理学史和地理学思想史。地理学史作为科学史的组成部分曾得到老一辈学人的关注,近代地理学史的研究成为近年的一个学术热点(详后)。
地理学思想史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学科分支。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年)是这一领域的典范之作。随后相关探讨一度沉寂,近年又涌出若干有关中国上古地理思想的佳作。如晁福林《〈礼记·礼运〉篇“殽地”解——附论“地”观念的起源》(《人文杂志》2019年第1期)指出,“地”的观念在商代尚处于象形思维的阶段,到西周时期才形成能与“天”相对应的“地”的观念。张惟捷《从卜辞“亚”字的一种特殊用法看商代政治地理——兼谈“殷”的地域性问题》(《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认为,商人在内外服观念之外,可能还存在一种对大邑商边缘的特定政治地理认识。
山川观念也是重要的地理观念。与已有的研究不同,牛敬飞《古代五岳祭祀演变考论》(中华书局,2020年)将五岳视为一个整体,对之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梳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周隋、唐宋四个时期国家礼仪中五岳祭祀的演变,并讨论了唐宋五岳真君祠和明清北岳移祀两个问题。谢一峰《天下与国家:试论南宋初年五岳祀典双轨体制的形成》(《史林》2015年第1期)则揭示了偏安东南的南宋王朝的山川观念,指出南宋初年的五岳祀典从起初的五岳四海四渎体系,演变为五岳四海四渎和南岳东海南海南渎的双轨体制。
对中国历史晚期地理思想的探索也取得若干成果,特别是对近代领海观念、疆域、版图概念的讨论。疆界的“内”与“外”是基本的地理思想,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马戎《中华文明的“内”与“外”》(《复旦学报》2016年第5期)指出,今天讨论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必然面临中国传统、现代国际法、现代概念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一些研究者试图回到传统中国的语境,澄清特定历史时期的“内”“外”观念及其演变。如王宏斌《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管辖问题研究——兼与西方领海观念比较》(《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具体分析了沿海六省内、外洋的范围,巡洋制度和内、外洋的管辖权,并考察了中国“外洋”与西方“领土”观念的异同。王春桥《明清云南西部边地土司“内外”分际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1辑)则讨论了云南西部边地土司的“内外”分际过程。
地名是地理思想的重要载体,李勤璞《“西藏”地名的起源》(《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考证了从元明时代“乌思藏”演变出汉文地名“西藏”的过程。这一过程实则体现了随着历史的演进,不同主体对于青藏高原地理分区认知的变迁。
(五)小结。历史地理学的各主要学科分支的建立由来已久,各个分支也发展出比较成熟的方法论。近年来,研究者试图在史料、方法和视角诸方面有所突破。沿革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各分支中受到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学者关注最多的分支。就沿革地理而言,以考古出土资料为主的新史料的运用,使得传统的沿革地理考证大大超出了清代乾嘉学者的视野,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基础的沿革地理学得以取得持续的进步。历史政治地理学的成果在历史地理学各分支中始终最为耀眼,周振鹤创建的中国政治地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历史政治地理着眼于政区地理要素的时空变迁,历史学界所提倡的“活的制度史”对历史地理学者而言其实并不陌生,将地方行政制度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际,正是历史政治地理的要义所在。由于历史地理学界对世界史诸问题较少涉及,因此在政治地理的三个尺度中,国际尺度方面取得的成果还十分有限。关于现代政治地理学的某些术语对于历史政治地理研究适用性的讨论仍相对薄弱。
其他的传统分支虽然取得了这样或那样的成就,但总体上还只是在已有的框架下有所细化和深入。或许只有对广义的历史学各专门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贡献,历史地理的独特性方能为学界所重视。
二、多学科合作与新手段的运用
(一)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时空变迁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本要求。基于这种亲缘性,考古研究者通常积极利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和成果,对考古资料做出新的解释;历史地理研究者则利用考古资料对一些传统历史问题展开新的研究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结合后产生的成果不仅更加翔实可信,而且可能带来新的历史认识。
确定文献记载的先秦古国的地望,往往需要结合考古学、文献学和古文字学。近年来,“曾国之谜”的成功破解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个案。考古发现的曾国与文献记载的随国到底是什么关系?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最早引出这一话题,并提出曾、随为一国二名的假说,引起考古、历史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并由此拉开了长达40年学术争论的序幕。根据曾、随活动区域相同、存世时间相近、同为姬姓、都以随(今湖北随州)为都城、春秋晚期之后都受到楚国礼遇且周代存在一国二名的习惯等,很多学者赞同一国二名说,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部分学者仍然坚持认为曾、随为二国。201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随州枣树林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曾国贵族墓地(《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考古》2020年第7期),其中曾侯宝夫人芈加墓的铜器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曾公求夫人渔墓的铜器铭文“唐侯制随侯行鼎”,充分证明曾即为随。这一发现为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曾随之谜”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再如,尹弘兵《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结合多年在汉东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对西周早期汉东地区的人文地理景观做出初步的复原,并在此基础上对昭王南征、西周在南方的经营及西周早期南方政治地理等进行了考察。
历史城市地理也是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合作的领域之一。李并成《唐代会州故址及其相关问题考——兼谈对于古代城址考察研究的些许体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3辑)结合作者的实地考察经验,提出了一种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与古城址考察三重证据相结合的方法。这一方法亦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借鉴。
讨论一些历史文献记载不足的领域的地理问题,不得不依赖以考古材料为主的实物史料,研究者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融通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两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如黄义军《中国古代瓷业的人文地理景观视角》(《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11期)探讨了人文地理景观理论对古代制瓷手工业地理研究的可行性与适用度。
(二)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生态史的结合。近年来,涌现了不少历史自然地理的新成果,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采用多学科的视角观察自然环境变迁。侯甬坚、杨秋萍《从历史地理学到环境史的关注——侯甬坚教授专访》(《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1期)指出,环境史的视角,使自然环境从历史的“舞台”变成了历史的主角;生态学视角的加入,则使研究者更加关注作为整体和系统的世界,探索人与自然,以及其他生命体的紧密关联。这方面的热门话题集中在气候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自然灾害的时空过程及其社会影响、水环境中的人地关系等领域。
气候如何影响历史是大众关心的热门话题,也是严肃的学术研究的主题。萧凌波等发表于英文期刊《全新世》上的文章《饥荒、迁徙与战争:晚明与晚清华北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与响应对比研究》(Famine,migration and war: Comparison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social responses in North China between the late Ming and late Qing dynasties,The Holocene,25-6,2015)讨论了晚明时期华北气候变化引起的饥荒、迁徙和战争及社会的回应。方修琦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科学出版社,2019年)则聚焦于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揭示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的过程与机制。
水环境变迁及其与人类的互动也是近年关注的热点。对历史上水体的复原是研究的基础,邓辉、卜凡《历史上冀中平原“塘泺”湖泊群的分布与水系结构》(《地理学报》2020年第11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大比例尺地形图、ETM遥感数据、DEM数据、土壤调查数据及古地图,系统复原了北宋“塘泺”的空间分布范围与内部水系结构。
水环境变迁中的人地关系为很多研究者所关注。贾长宝《从大野泽到梁山泊:公元12世纪末以前一个黄河下游湖泊的演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对大野泽—梁山泊在12世纪末以前的演变史作了剖面式分析,尝试揭示黄河影响其下游湖泊演变的一般规律,并探讨了鲁西南地区黄河、湖泊及人类活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程森、刘立荣《省界错壤与洪灾调适冲突——以明清卫河下游直鲁交界地区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2辑)采用美国地理学家吉尔伯特·F怀特的洪灾调适理论,以卫河下游直鲁交界地区为例考察传统时代政区边界与洪灾调适的关系。孙景超《宋代以来江南的水利、环境与社会》(齐鲁书社,2020年)从潮汐影响入手,复原了历史时期感潮区的变迁,通过对感潮区水利问题的探讨,对江南地区的农业环境、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了深入分析。
(三)数字人文与量化研究方兴未艾。关于数字人文方面的进展,除了为学界所习用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自2000年以来,一些新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陆续建成。以GIS为中心的数字人文技术持续运用于政区、交通、城市、文化、家族网络、古籍、土地利用、灾疫等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仅举一例加以说明,张萍《GIS技术与二千年丝绸之路道路复原研究的新思路》(《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2期)从路网体系中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性质判定与时空起止界面、GIS定位与二千年丝绸之路道路体系复原三个方面介绍了“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的新思路。这一系统的建成,不仅能为相关历史研究提供服务,而且有望发掘出更多富有前景的研究论题。
随着数字人文的开展,以往靠泛化的定性分析难以着手的问题,出现了可能的解决路径。如钱超峰、杜德斌《北宋官僚家族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基于CBDB和CHGIS的考察》(《历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2期)利用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和中华文明时空基础框架(CCTS)等数据库,揭示出北宋官僚家族网络的空间结构特点及其演变趋势。
(四)小结。多学科合作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掘史料所包含的多个层面的信息。但是,多学科合作并不是两个或数个学科的简单叠加。它要求研究者恰当理解不同学科解读史料的方法,或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或纠正其方法上存在的误区。例如,历史地理学家在利用考古资料时,一方面须对其可靠性有所把握,另一方面,还要理解考古资料解读历史问题的长项与局限。再如,虽然从环境变迁角度解释社会变迁是十分有趣的视角,但也要警惕掉入环境决定论的窠臼,须对环境因素的决定作用做出恰当的评价,人地关系及人对环境的调适始终应当作为历史地理学关注的重点。
新技术为历史地理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其局限与边界也值得研究者思考。正如韩茂莉、佟萌《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辑)指出的那样,“中国历史文献属于定性记述,遑论大数据,即便GIS技术、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均需要一定数量的数据支撑,如何获取数据?这是历史地理面临的挑战”。GIS作为一种地理分析和地图展示手段,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但它在历史地理领域的运用,仍然是建立在对历史文献的精心考证的基础之上的。它对地理现象的揭示取决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及问题本身的价值,并不能取代研究者自身的思考。
三、新热点的出现
郑星《1987—2014年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现状——基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文献计量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2辑)通过计量分析发现,1987—2014年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所发表文章集中在春秋、唐代和明清三个时段,其内容除了传统的地理志和历史地图集外,行政区划变动、人地互动关系及农业生产状况、环境变迁和生态治理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对照郑文,可以发现近年来出现的若干学术热点。
(一)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理问题。中国历史的近代化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2014年,蓝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思考》(《光明日报》2014年9月24日)呼吁加强对近现代历史地理的研究。近年来,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小进展,其成果涉及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尤以政治地理、城市地理、区域研究、地理学史最为突出。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在政治地理国际维度方面,一些研究者针对近代或当代国际疆界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见解,如李花子《清代中朝边界史探研——结合实地踏查的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年)综合利用中韩日三国的文献资料,结合作者多年的实地踏查经验,对清代以来的中朝边界史进行了深入探析。
以往的政治地理研究较少关注民国以来的政区变迁,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似有井喷之势,其中不乏力作,如徐建平《中国近现代行政区域划界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对清末民初的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政区边界法定化过程进行了研究,展现了近现代政区边界从“界限”到“界线”的过程,并分析了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因素。省界纠纷的个案研究也很丰富,例如,王晗《地方治理与利益诉求:民国初年陕绥划界纠纷研究》(《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4期)对民国初年发生的陕绥划界事件进行了研究,揭示了省界纠纷中所涉及的地方治理与利益诉求。此类研究的开展,得益于丰富的近现代史料,同时为我们理解王朝时代的同类问题提供了参照。
城市是近代化的前哨。城市的近代化体现在城墙的拆除、城市空间、城市文化转型等诸多方面。以往对中国城墙的研究,侧重其修筑史与具体形态,近代化视野下的城墙研究则更加关注城墙拆除背后的思想观念。例如,贾长宝《民国前期北京皇城城墙拆毁研究(1915—1930)》(《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对民国前期北京皇城城墙的拆毁事件进行了梳理,指出这一事件与北京城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当局的市政建设理念存在密切关系。
城市空间的近代化转型也是一个颇受关注的热点。例如,唐晓峰、张龙凤《新华街:民国北京城改造个案述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3辑)讨论了民国初年北京城改造中开辟南、北新华街的政治、社会意义。从新华街计划的实践中,既可以看到城市改造的方向,也可以看到北京城传统空间特征在近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性。熊远报《八大胡同与北京城的空间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妓院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则讨论了另一类城市空间——红灯区在近代的形成过程,其中涉及清初满汉分住、清末新政及近代化过程中公共性社交区域等重要历史问题。
区域研究往往需要结合生态、人群、政治地理、交通等各种要素。谢宏维《斯土斯民——湘赣边区移民、土著与区域社会变迁(1600—1949)》(人民出版社,2019年)讨论了1600—1949年间湘鄂赣边区由外来移民引起的矛盾冲突,揭示出移民与土著,二者与国家,二者内部及各级政府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李发根《荒地、巨镇与村落:国家意志与近代安徽和悦洲的百年轮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2辑)梳理了地处安徽长江上的和悦洲近百年来从荒地到巨镇再到村落的巨变。
近代地理学史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主要包括晚清学者的边疆研究,外国人在中国的地理考察与测绘,近现代地理学派、学会与学人研究,民国时期地理教学的研究等。关于晚清学者的边疆研究,代表作如史念海、王双怀《清代学者对于西北史地之研究及其著述》(《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1期);关于外国人在中国的地理考察,代表作如侯甬坚、韩宾伟《20世纪初期芬兰人马达汉入疆考察细节及其分析》(《历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1期)。近现代地理学派、学会与学人研究,成果颇丰,代表作有谢皆刚《清季中国地学会的边疆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4期),范今朝《“史地学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1辑)等。张雷在英文期刊《历史地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洋墨水:民国的地理留学生》(Foreign Ink: Student Mobility, Overseas Training and Chinese Geography, 1912-1952,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68,2020)主要探讨了1912—1952年间中国地理留学生移植欧美地理学范式所遭遇的内在张力。
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理研究大大受益于档案的解密和成套史料的整理出版。同时,相比古代文献,近代史料能提供更多可资量化分析的数据,与数字人文的发展相得益彰。许多成果体现了这一特色。长期以来,学界未能重视近代历史地理的研究,作为一种代偿,想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近代历史地理的学术成果还将持续涌现。
(二)基层社会治理。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也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它与历史地理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县以下基层区划的设置与实际运作。其中以鲁西奇和包伟民的成果最为突出。
乡里制度是古代基层区划的核心。鲁西奇的一组文章分别论述先秦两汉、隋唐、辽金元时期的乡里制,其中《辽金时期北方地区的乡里制度及其演变》(《文史》2019年第4辑)系统梳理了辽金时期北方地区的乡里制度,并对辽金史研究中的胡汉二元方法之于乡里制度研究的适用性进行了反思。包伟民的一组文章涉及近古时期的里制及宋代的乡制和村制,《中国近古时期“里”制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揭示了有关宋代基层组织的历史文本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指出,以地方志为主的存世宋元文献关于农村地区基层组织的记述绝大多数是以乡—里排列的,但实际上到北宋中期,延续自前代的乡里制已被废弃,乡成为一种地域单位。
皇权是否下县?这一问题近年为学界所热议。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探讨了清代县辖政区的渊源、类型、空间分布及其与基层行政、法律实践、市镇管理、钱粮征收、州县置废、地区开发的复杂关系,力图从中国本土行政实践中寻找到清末以来县以下区划的历史渊源,对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皇权不下县”等相关理论假说也作了反思。鲁西奇《“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则认为,乡里制度既是王朝国家实现其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性安排,也是王朝国家政治控制权力在县级政权以下的延伸。
总体上看,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以传统时代为主,如何在这一话题内加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为现实社会提供思想资源,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边疆民族历史地理。近年来的新趋向包括对边疆概念的理论反思,以及苗疆、改土归流等政治地理意义上的边疆治理、民族人口等地理研究。
何为边疆?这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问题。例如,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对“边疆”一词作了语源学的梳理,指出当今社会对“边疆”的界定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与“国界”密切联系在一起且在 “边疆”之外还有了一个 “民族地区”的概念。吕文利《何谓“边疆”——论中国“边疆”概念的三重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从西方空间理论中得到灵感,认为现代中国的 “边疆” 概念具有三重空间上的意义,即地理意义的第一空间、历时性的第二空间及主体认识上的第三空间。
除了众多关于边疆民族地区地名考证的文章外,政治地理意义上的边疆治理也较多地被研究者所关注,如陈文元《边墙格局与苗疆社会——基于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历史学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梳理了清代苗疆边墙的修筑原因与经过,并与明代进行了对比。周妮《明清时期“苗疆”土司与“流官”政区疆界纷争与化解——以黔楚蜀交界地区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3期)讨论了明清时期今湘鄂渝黔交界地区的土流疆界纷争通过改土归流得以解决的过程。
历史时期非汉族人口问题是中国人口史研究的一大难点,安介生《略论清代至民国时期户籍管理与民族人口——以川西松潘为例》(《历史地理》第32辑,2015年)通过搜集、整理、比较留存下来的不同时期各民族户口资料,对川西松潘地区的民族户口进行了分析和估算,提出了一条研究历史民族人口的可行路径。
边疆民族是历史学界的热门话题,除了传统的沿革地理考证,以及历史政区、交通、人口、经济地理等方面的个案研究外,如何扩大视野,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角度发现其中的地理问题,似有待着力。
(四)地图学史。近年来,地图学史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其研究进展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地图学史研究的理论思考;二是对存世地图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对中国与周边地区地图交流史的研究。
美国学者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姜道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批判了以部分“代表性地图”为依据,过于强调古代地图数理维度的传统研究取向,提出了一种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研究中国古代地图的新范式。在这一思想的启示下,中国学者也展开了方法论的反思。如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 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对“科学取径”的两个支柱命题“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进行了质疑。孙靖国《〈江防海防图〉再释——兼论中国传统舆图所承载地理信息的复杂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也回应了以往地图史研究中的“科学取向”,指出中国传统舆图往往依绘制者和使用者的需要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其所展示的地理信息或存在时间上不同步的现象。
对存世古地图的整理和编目仍然是当前的一个重点,近年来产生了一大批这方面的成果。李孝聪《中国古旧地图的编绘、收藏与利用》(《中国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年)是一篇具有指南性质的文章。文章详细讲解了中国王朝时代、特别是清代舆图的编绘与收贮、中国古旧地图的流传及在中外机构的收藏情况。
对存世古地图的研究也涌现出不少佳作,如龚缨晏《〈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驳李兆良的相关观点兼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通过还原《坤舆万国全图》的绘制过程及对相关中外史料的严格辨析,反驳了李兆良提出的《坤舆万国全图》绘制于1428—1430年、乃郑和为七次下西洋而备的观点。近年,韩昭庆及其团队发表了一组有关《皇舆全览图》的文章,其中《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及意义》(《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指出,《皇舆全览图》是少有的采用现代测绘方法绘制的古代舆图,因此有望将其进行数字化处理,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历史研究。
对中国与周边地区地图交流史的研究也有若干出色的成果。例如,姚大力《〈大明混一图〉上的两个印度》(《复旦学报》2020年第1期)通过对《大明混一图》上出现的两个印度的考释,思考了中西地图文化的交流问题,即伊斯兰世界的地图作品传入中国后如何被模仿、思考和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制作出不同于原图的新地图。李军《跨文化语境下朝鲜〈天下图〉之“真形”——兼论古代地图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美术大观》2020年第12期)对朝鲜《天下图》的学术史进行了细密的梳理和辨证,从三个方面对《天下图》进行了最新解读,重点分析了《天下图》对中国历史资源的利用与改造。
地图学史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热点,其研究者不限于历史地理学界,而是分布于历史学、美术史、建筑史、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因此,地图学史的研究也展现出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但总体上,近年来仍然主要局限于对中国古代存世地图的研究,只有个别学者涉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图史。加入世界地图学史的研究队伍,展示中国学者的国际视野,仍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四、展望
综合以上分析,今后可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其一,加强明清以前各代的历史地理研究。近年来的成果在时段分布上很不平衡,以《历史地理研究》为例,2015—2021这6年间共刊发研究论文272篇,其中明清和近代为134篇,约占50%;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各代都在10%之间;而通代的研究不到5%。明清以前的历史地理研究仍显不足。
其二,加强中外历史地理成果的互介。中国历史地理学一直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近年来也有不少中国历史地理的英文著作译介到国内。个别学者还出版了英文历史地理专著,如丁雁南等合著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China: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rb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18),但见诸外刊的中国学者撰写的历史地理论文主要集中在历史自然地理,特别是历史气候领域,其他分支的文章比较少见。
其三,加强外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历史学的必然要求,历史地理学也不例外。尽管个别研究者已开始关注外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动态,但中国学者的研究涉及的主要是中国周边国家,以日本、朝鲜和越南居多。个别文章涉及西方,如邵大路《塞琉西亚建城考:早期希腊化城市与帝国统治》(《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关于希腊化时代早期城市塞琉西亚的研究,何凡能等《中美过去300年土地利用变化比较》(《地理学报》2015年第2期)对中美两国过去300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做出的对比分析。但总体来讲,这方面的成果迄今还相当零星。近年来虽然引进了少数西方历史地理的经典,如美国学者克拉伦斯·格拉肯《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从古代到十八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梅小侃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但这些著作尚未在中国内地历史地理学界引起太大的反响;而且一些堪称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之作的西文书籍尚未得到译介,这种状况,对于一门产生于近代化过程中的学科——中国历史地理学而言,的确有几分尴尬。
最后,近年来新热点的出现与国家的现实需要和学术导向息息相关,体现了历史地理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历史地理学初创之际即受到边疆危机的推动,学者们积极展开边疆史地研究。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非常重视历史地理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如侯仁之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谭其骧关于黄河、云梦泽和上海成陆问题的研究,以及史念海对古都与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研究,都体现了历史地理学经世致用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今天并没有过时,相反地,应该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
附记:感谢孙靖国、苏辉两位老师为本文的写作提供的诸多帮助。
信息来源
《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6期,第21-32页。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欢迎专家学者、相关研究机构给历史地理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平台投稿,传播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动态、学术研究成果等等,惠及学林!
投稿邮箱:852565062@qq.com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历史地理研究资讯):前沿动态 | 黄义军:历史地理研究的新趋向(2015—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