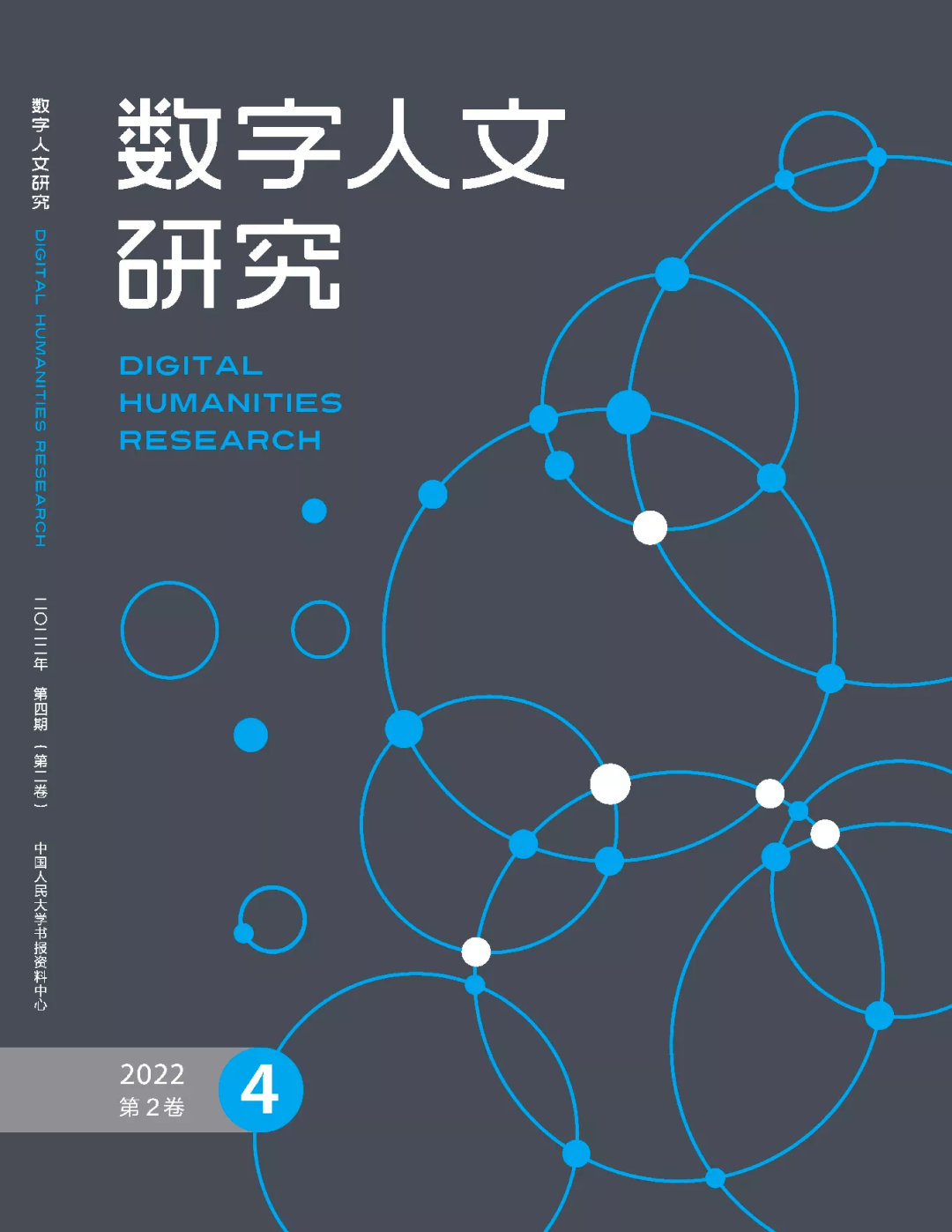0 引言
作为数字人文三位一体发展中的一足,教育与科研、实践并驾齐驱,相得益彰。继承数字人文的基因,数字人文教育天生带有很多与众不同的新特质。循新探新,走一条全新的教育之路,不仅符合数字人文的本质特征和人才需求,还有可能产生一定的“鲶鱼效应”,搅动高等教育的池水,激活新型教育模式的成长。数字人文教育与新文科理念有深层的吻合和呼应,如王丽华、刘炜所言,“数字人文之于传统人文的‘新’与新文科的‘新’是同向同行的,都具有创新指向,而数字人文与新文科的相互作用将带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浪潮。”
纵观国内外现有的数字人文教育,结合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情况,本文将数字人文教育的“新”概要归纳为教育格局之新、目标之新、结构之新和角色之新,新的理念贯穿在上述所有的新意之中。这些新特征并非数字人文教育所独有,但在其处尤为鲜明,且诸新相映,相辅相成,使之成为颇具典型性的高等教育“新物种”。由于数字人文自身尚处于成长时期,对于教育活动的要求尚未清楚透彻,对于人才质量的检验也尚无全面理性的长反馈,因而我们对于数字人文教育的认知还有很多主观和表浅成分,加上长期教育工作的惯性,往往以为不过是新开一个专业而已。在这个阶段,边发展、边思考、边探索、边改革,可以看到一个符合数字人文人才培养要求的新型教育体系的孕育成长。
高等学校的数字人文教育始于2001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开设的研究生课程,2005年伦敦国王学院首设数字人文博士学位。目前除本硕博教育之外,还有辅修课程、通识课程、证书教育、暑期学校等多种方式。
数字人文在当前学科版图上的定位难题自然传导到数字人文教育之中。传统教育项目通常有较为清晰的学科归属,设置在一个学科门类之下,即使国外大学没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之类的体系划分。数字人文教育的多学科属性,使之失去了归属上的共识,实际做法大体是一所高校从哪个学科进入就把这个教育项目放在哪里,呈现出极大的自由度和多样性,人们很难确认它的学科隶属关系。根据国际信息学院联盟(iSchools)数字人文课程组2020年9月对全球数字人文教育的学科分布状况调查,开设数字人文教育项目数量排名前10的学科领域是:数字人文的理论与方法(Theory and Methodology) 148个,艺术与文化研究(Arts and Cultural Studies)126个,语言学(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Studies)118个,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107个,历史学(History)103个,文学与哲学研究(Literary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99个,图书馆学情报学(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55个,媒介与传播学(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51个,社会学(Social Science)42个,考古学(Archaeology)39个,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学科有所分布,也有学校由跨学科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导。中国目前的数字人文教育项目从信息资源管理、文学、历史、艺术、传媒等不同学科切入。中外数字人文教育分布的学科横跨传统人文、社科、理工不同类别,不同的教育项目各有侧重,大多带有所在“学科家族”的特点,从事数字人文教育的学术共同体结构也十分复杂,其学科背景之多样是前所未有的。
这样的数字人文教育分布状况,打破了长期以来根据教育内容进行学科门类归入的办学思维;在中国主要按照一级学科管理的体制下,多学科课程、团队规划建设和管理、教师工作量认定等也出现一些新问题。专门针对数字人文某一领域的教育,如数字历史、数字艺术等,尚可以放在现有学科框架下,综合的数字人文则难以归位。202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并设置了若干交叉学科,对其内涵界定为:“交叉学科是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通过深入交融,创造一系列新的概念、理论、方法,展示出一种新的认识论,构架出新的知识结构,形成一个新的更丰富的知识范畴,已经具备成熟学科的各种特征。” 尽管数字人文教育尚未成熟,如果必须进入一个一级学科的话,依上述解释,还是进入交叉学科相对合理,在其多学科交叉教育中面临的大量新问题需要在教育实践中逐一应对和破解。
新文科、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等“四新”建设,是2019年以来教育部倡导的高等教育改革战略。从数字人文所解决的问题性质看,划归“新文科”是有道理的。“新文科”与传统文科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不仅是文科之间的交叉,还包含与其他门类学科的“杂交”。数字人文教育涵盖文科很多领域,并与理工科深度交叉,因此在新文科建设中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辐射性价值。当然,如果某高校从计算机应用角度把数字人文看作是“新工科”的元素也未尝不可。
2目标之新
数字人文教育的终极目标是给学生留下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大多数专业教育追求以清晰的知识边界、确定的知识结构和成熟的知识体系为基础,向学生传授具有稳定内核的专业知识。而当前的数字人文教育却与此相距甚远,各国高校在探索其理论体系、技术体系、应用拓展和学科建构的基础上个性化发展,具有明显的“三无”特征。一是没有经典理论和权威定义,“数字人文”概念开放包容,广为流传的伞状概念(Umbrella Term)和大帐篷概念(Big Tent),表明其不寻求定义和边界的确定。“学科边界在教育领域远比在科研领域的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学科边界的不确定对于教育教学组织与活动的挑战更多更大。或许因为高等教育惯常以基本确定的学科边界设置专业和课程体系,“新文科”对于既有学科边界的“跨越”与“混合”带来专业、课程、教学形式的一系列不适应,数字人文的弱边界感、对教育目标的再认定即缘于其中。二是没有已形成共识的学科知识范畴和课程体系。由于数字人文领域的广泛性,各国各高校的数字人文教育大多在人文知识、数字技术方法和项目实践三大类之下各有切入点,面貌各异。中国人民大学开办数字人文教育时参考了12所国际知名大学的教学方案,但几乎找不到相近的“模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相继开设必修和选修课程281门(地理、教育、公共管理、社会、统计、经济、信息管理、计算机、建筑、艺术、语言、文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涉及15个学科。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的本科有28门主干课,涉及数字政治、数字经济、数字文化、数字方法等;硕士课程40门,涵盖数字人文理论、文化与社会大数据、数字技术与方法、数字文化与社会、数字资产与媒体管理五个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数字人文硕士专业的培养方案设有21门专业课,涉及数字人文理论、人文知识、资源管理、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等方面。三是没有标准答案。不仅在数字人文的价值、作用、对人文学术的影响等重大问题上存在不同视角的认知差异,有关方法与技术的应用亦存在基于不同需求、不同审美的相异认知和判别。如同世上没有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一个数字人文项目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都是针对独立的目标而设计和实践的结果,并没有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恒定模式。因此数字人文不可能像某些专业、某些课程那样,做出题库和标准答案考核学生,因为那个标准答案根本不存在。
数字人文教育的这种“三无”特征来自于数字人文与生俱来的“不安分”,《数字人文宣言2.0》指出:数字人文“拥有一颗乌托邦的内核,这一内核是由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反主流文化——赛博文化以来的血统所建构而成的。这也是为什么数字人文要重视文化和学术的开放性、无限性、开阔性、民主性的价值的原因。”因此,数字人文课程教学目标不能定位于讲解和传授确定的知识,而是引导学生走进、理解、分析、辨别、思考、质疑,甚至颠覆,提升认知和思维能力;调动学生把自己的头脑设定为开放模式,拥抱开放的数字人文知识与前景。
这样的教育目标需要渗透到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自微而至著。比如把概念引导转向实例引导,面对没有确定边界的数字人文“大伞”,不追求概念的确定统一,而是通过大量案例实现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认知过程。学生们在形形色色的数字人文项目及其实现路径中建立起来的数字人文框架,具有丰富的多元性、合理的包容性和生长活力。又如把结论引导转向思辨引导,传统人文学科即具有深刻的反思性,将质疑思辨作为一种追求,因而数字人文的反思性特点更为突出。面对数字人文理论和实践中纷杂多样且充满争议的思想观点,教师要有意识地排除习惯性“结论预设”,不轻易做正误判断,特别要注意避免自身知识结构可能带来的认知局限和思维定式,要把数字人文进展中的各种思想观点、技术方法、效果及评价交给学生,诸如数字人文对于人文学科的利与弊,数字技术方法可以/不可以解决哪些人文学术问题等等,使其从不同立论、不同现象中汲取数字人文理论与方法的丰富与多元性,同时从中学习批判性、反身性思考的思辨过程,自主建立数字人文的认知框架。
由于数字人文知识的多元复杂,数字人文项目的独特创新,数字人文教育中的思维训练非常重要,须贯穿于知识学习的全过程。数字人文的发展演进是一个复杂的探索过程,与传统人文学术有深层的继承、拓展和创新,方向性和方法性并重,对数字人文学者、从业者的思维能力和知识储备要求并重,国内外数字人文教育工作者对此体会颇深。2022年中国数字人文年会数字人文教育论坛上多位参会者强调防止把数字人文教育工具化,要把思维训练放在重要位置,作为培养学生的目标之一,如交叉思维、数据思维、计算思维、通观思维、创新思维等,特别注重批判性创新思维的培养。王丽华、刘炜曾在文章中统计了大卫·M.贝里和安德斯·费格约德合著的《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一书中“批判”一词的出现频率,作为名词(critique)出现了55次,作为形容词(critical)出现了180余次。iSchools数字人文课程组对全球数字人文教育的调查中,教育工作者提及的“批判性”(critically)是第二大高频词,仅次于“理解”(understand)。可见批判性思维在数字人文教育中的特殊地位。
3结构之新
学科交叉是数字人文最鲜明突出的特点,也是与新文科导向最深层的契合。《数字人文宣言2.0》指出:数字人文的体裁是M型的,即混合(mix)、匹配(match)、捣碎(mash)、展现(manifest)。对于这四个词在数字人文中的表现可以有多方面解读,至少可以表明它的非单一、非固化结构和方法。数字人文涉及众多学科,跨越若干学科群,形成一种大跨度、多线索、深融合式的交叉,引发教育教学结构的多层面变化,及至教育功能、教育理念和教学组织的变化。
首先是课程结构的变化。全球数字人文教育布局和定位多样性中所具有的共同性,就在于任何一个项目的课程体系都是多学科知识的交叉组合,都需要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相辅相成,总体上是由人文知识、数字技术方法和观察实验实践三个板块组成,每个板块中有不同的课程配置。一方面,人文知识和数字技术方法都十分宽广,前者广博深厚需持续积累,后者专精严密并不断进化,每一个数字人文教育项目都不得不面临内容和深度的选择。另一方面,两类知识的拼盘固然有用,但是其融合程度才是决定数字人文价值和功能的根本,而教学实践则是对上述配置和融合的直接检验,是每个数字人文教育项目面临的更大挑战。安妮·伯迪克等人在书中用专节讨论了数字人文专深结合问题,指出数字人文“如何能够在自由无边的网络化学术中注入深度钻研?刺猬的深度因其严谨性而激励人心,狐狸的好奇心因其活力而令人惊喜”“我们的目标是结合二者,创造出既能够广博也能够深究的‘刺猬狐’”。
各国的数字人文项目均主要面向本土文化,我国的数字人文发展应以推动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中华文化全景呈现和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为宗旨,因而在数字人文教育的人文知识板块中,要着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承,而中华文化蕴藏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语言等不同门类的知识中,每一个教育项目需要根据特色定位、项目性质与课程时长等因素选择课程安排和知识传授方式,这也是数字人文课程结构需要设计的一个点。
由此对教师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提出了新要求。在现有的学科建制下,教师的专业化、甚至方向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少有老师具有数字人文所需的文理相通的大跨度知识储备。起初大多数数字人文教育项目主办方寄希望通过不同学科背景教师承担不同课程来应对文理交叉的课程结构,然而,当教学过程中需要深入解读数字人文实现原理,剖析数字人文案例,指导学生策划实施数字人文项目时,立刻被知识短板所困,这个短板不仅来自知识盲区或一知半解,同时来自新对象、新方法对传统学科知识和思维习惯的冲击。相比传统人文研究,数字人文在兴趣驱动、问题驱动中加入了数据驱动,在定性研究中加入了量化研究,在主观感悟、思辨与灵感中加入了归纳与实证,在观察、演绎方法中加入了对象要素的统计、归纳和抽象,在关注因果结论的同时加入了多层面相关关系分析等等,即使人文学科背景深厚的教师在数字人文中也需要面对很多新的研究议题和方法。相比计算机较多应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规则数据,数字人文则需要数字技术处理更多的模糊性、隐含性、不确定性、主观性、情感性要素,即使是数字技术方法的高手也常困于人文功底不足而难于设计项目功能与实现路径,甚至难于开展数据加工处理。毕竟数字人文是数字与人文的合体,教育者拥有复合性的知识基础才能理解透彻,如王涛教授所言,数字人文是一幢高耸的学术大厦,它是由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学、计算机等不同房间组成的。初始阶段的数字人文教育可以通过浅层次的知识对接方式推进,随着教育活动的纵深发展,终究需要教师的知识结构复合化,如果说数字与人文1+1的知识结构甚难达到,至少需要具有1+0.5的结构,才能比较有底气地胜任数字人文教学与指导。也就是说,数字人文教师队伍的配置,要以“术业有专攻”为基础的不同专业教师参与和每位教师一定程度的知识复合化两路并行。
数字人文教育必须引导学生形成文理兼备的跨学科知识结构。目前,数字人文本科教育的学生来自于文理分科,通识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学生则来自于不同专业,既有知识结构或知识偏好都有明显的差异和局限。大多数人文专业学生的数字技术基础薄弱甚至对其有些抵触,而不少理工科(也包括一些社科专业)学生的人文功底薄弱甚至缺少兴趣。虽然参与数字人文学习的学生知晓这个领域的跨学科性,但长期的分学科训练使得一些同学给自己的学习能力打上了某种标签或设定某种心理暗示,对于不擅长的领域缺少足够的动力和信心。常看到人文基础见长的学生偏重数字叙事类项目而规避专精的量化方法,理工基础见长的学生则倾向于选择数据处理和计算类项目而规避需要功力的史料阅读。可见,学科交叉无论之于教或是之于学都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儿,这是数字人文教育绕不开的的挑战。
数字人文教育的结构性变化需要结构性应对,每一个数字人文教育项目都需要做专门设计,除了必要的理论课、方法课之外,可根据每个教育项目的定位,如侧重于数字历史、数字文学、数字重建、数字艺术、数字记忆等安排相应的特色课程,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安排一些选修课,给学生宽口径、个性化发展以帮助。为此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混合编队”,承担不同方向的课程,同时在描绘出整个项目知识图谱的基础上制订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实现不同课程知识的互补并减少重复,倡导教师互相听课、互相请教和项目合作,逐步形成人员结构和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引导和帮助学生探索跨学科学习的路径,鼓励学生走出舒适区,勇于挑战自我。通过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分类辅导,不同学科学生组成合作团队等方式帮助学生搭建合理的、有跨度的知识结构。
4角色之新
大众参与是数字人文在改变知识生产方式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它弱化了知识生产者的资历资格条件,弱化了知识权威的判定作用,弱化了知识发布壁垒,吸引大众以各种方式参与知识的生产与繁荣。这种开放性不仅来自数字媒介的承载和传播能力,也来自大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数字文化创作能力。因此,在数字人文教育中,教学方式以及教师和学生的传统角色都将有所改变,从教师灌输式知识投喂转向真正的学生参与式学习。
参与式学习是高等教育多年倡导,并在新文科建设中着重强调的教学方式。早在2002年,叶澜教授就指出教学的内在逻辑是“多向互动与内在生成”的,“互动”强化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的多向参与、交流、关注以及合作的模式,“生成”即共同创造新的资源、活动、思想、观点,逐步朝向教学目标“生成”。对于数字人文而言,这种多向互动与内在生成更为必要,如安妮·伯迪克等人所言:“数字人文的迭代特性造就了一个复兴本科生核心课程的千载难逢的时刻,这些课程使他们在文化资料的生成和保存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这种新的文化生产为探索人类的文化遗产和想象未来的可能性开创新的重要空间。”上述中外学者的两段论述有着内在的思想吻合,“互动”即为“参与”和“利益相关”,“生成”即为“文化生产”,二者都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角色和态度,在数字人文教育中,这种教师、学生双主体的理念和模式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落地。
数字人文教育的双主体理念和参与式学习方式与该领域强烈的实践性密切相关,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理论到理论的循环中掌握数字人文真知,每一个数字人文项目都是对数字人文原理的独特诠释,哪怕是失败的项目也会给学习者重要的启迪,因此国际数字人文联盟的年度奖项中始终设有“最佳数字人文失败案例之调查研究”单项。数字人文教育需要培养学生在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实践创作与理性思考等构面之间来回穿梭的意识和能力,被称为“折线型教育”,而这种“穿梭”必然是学生的自主行为,是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的亲身实践和独立思考,不可能在“被灌输”中完成。
如同跨学科学习一样,参与式学习也是一桩知易行难的事儿。习惯了你讲我听、你教我学、你考我答模式的教师和学生都需要有所调整和改变。单向讲授在学生理解、消化、吸收学习内容和知识的内化方面效果受限,而参与式有利于学生打开思索的闸门,去深入思索乃至发现。在数字人文这样的交叉领域中,如何调动学生参与课程学习和建设?如何让学生用批判性思维领悟数字人文的思想、观点、方法和效果?如何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何组织学生有效地参与数字人文实践?如何让学生尝试共创分享和团队合作?这些都需要在教学方案中精心设计和实施。
所谓“双主体”“参与式”,就是要把原本完全掌握在教师手中的资源和能动性交给学生一部分,实行“开源”教育模式。比如把有关论点和争议交给学生,让学生思考判断,提出自己的见解;把教学案例、数据集、文献集交给学生,让学生阅读、评论、参考;把检验学习效果的“命题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自主项目设计中全面展现创新思维和实现能力,理解数字人文的价值和项目流程等等。为此,数字人文教育项目要做好充足的资源准备,除了建立案例库、文献库之外,最好能够搭建开放持久的实践平台,提供各种类型的项目参与机会和课内课外的创新指导,如此,学生的主体性感受和学习效果会得到明显提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1月的在线调查,国外高校除了大量跨学科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之外,已建设数字人文实验室24家,为学生的参与式学习和实践提供了稳定、良好的条件。中国人民大学积十年之功搭建了“北京记忆数字资源平台”,让学生的优秀项目有了稳定的发布平台。学生在自由使用各类教学资源的过程中还会将各自发现的资源添加进来,形成教学资源的开放式滚动充实。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获得数字人文荣誉学位的本科生这样表达参与式学习的感受:“数字人文课程像埋在深厚土壤中的一粒种子,当我们用不同的营养液去浇灌它时,可以期待她结出不同的果实,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总之无限可能!”。
5 结语
20世纪初,列宁谈到了“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问题,简单说来,就是自然科学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以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对社会科学发生积极的影响和渗透,从而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进步。21世纪兴起的数字人文则是自然科学向人文学科及人文学科向自然科学的双向奔赴,相互影响和渗透,这正是新文科追求和探索的道路。全球数字人文教育正处于蓬勃发展期,数字人文以其文理融合、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以及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创新等特点,与我国高等教育新文科建设多有契合之处,成为探索新文科理念的一片试验良田。在建构中国数字人文自主知识体系,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进程中,数字人文教育是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也应该作出独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