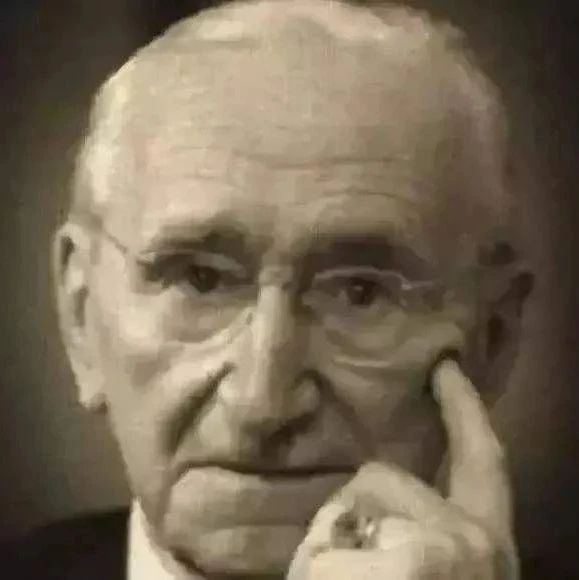

言不顺,……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
语言是行为的指南
所有人,无论是原始人或文明人,要想使他们的感知变得有条理,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语言使他们赋予这些感觉信号的特性。语言不仅能使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体分为不同的物体,而且能使我们根据自己的期待和需求,对不同标记的无限多样性的组合进行分类。这种标记、分类和区别当然经常是含混不清的。更重要的是,语言的所有用法都含有许多关于我们所处环境的解释或推理。正如哥德所承认的,我们以为是事实的,其实已经是理论:我们对自己环境的“所知”,也就是我们对它们的解释。
于是,在对我们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便出现了各种困难。例如,许多普遍认可的信念只是隐含在表示它们的用词或句子里,可能绝对不会成为明确的信念;于是它们也绝对不会有受到评判的可能,结果是,语言不仅传播智慧,而且传播难以消除的愚昧。
同样,由于一套特定的词汇本身的局限性及它所具有的含义,要拿它来解释与它历来习惯于解释的东西有所不同的事物,也是很困难的。不仅用原有词汇解释甚至描述新事物是困难的,而且要想把语言以某种特定方式做过分类的东西再进行分类也不那么容易——特别当这种方式是建立在感官的内在特性之上时。
鉴于这些困难,我们的词汇以及附着于其中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我们是用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然而,对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以及人类在其中相互作用仍然有着深刻影响的传统词汇,还有那些根植于这套词汇中的理论和解释,在许多方面一直是非常原始的。其中有许多是遥远的年代形成的,那时我们的头脑对我们感官所传达的东西,有着十分不同的解释。所以,当我们学会了许多我们通过语言而知道的东西时,每个词的含义会使我们误入迷途:当我们尽力要表达我们对某一现象的新的和更好的理解时,我们继续使用着含有过时含义的词汇。
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及物动词使无生命物体似乎具有某种思维能力。天真或无知的头脑,当它感觉到运动时,总是以为有生命存在,同样,当它以为存在着某种目的时,也总是设想存在着思维或精神活动。以下事实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进化似乎在每一个人类思维的早期发展中重复一次。
皮亚杰在《儿童对世界的认识》一书中写到:“儿童最初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目的。”只是在第二个阶段,头脑才开始对事物的目的本身(泛灵论)和造物者的目的(造物论)加以区分。泛灵论的含义附着在许多基本的词语之中,尤其附着在那些表示产生秩序的现象的词语之中。不仅‘事实’本身,而且‘造成’、‘迫使’、“赋予’、‘选择’以及“组织这些在描述非人格过程时必不可少的词语,仍然使许多人联想到人的行为。
“秩序”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例子,在达尔文之前,它几乎被普遍用来暗指存在着一个行动的人。在上个世纪初,甚至像边沁那样有名望的思想家,也主张“秩序以一定的目的为前提。”可以这样说,在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理论的“主观主义革命”之前,对人类创造力的理解一直是受着泛灵论信仰的主宰。直到19世纪70年代,在对竞争中决定的市场价格的引导作用有了更清楚的理解之前,甚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没有完全摆脱泛灵论的影响。
甚至今天,除了对法律、语言和市场的科学研究之外,人类事务的研究仍然被一套主要源于泛灵论思想的词汇控制着。最重要的例子来自那些socialism作家。人们越是仔细审视其作品,就越清楚地看到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更多地是在保护泛灵论的思想和语言,而不是对其进行改革。以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传统将“社会”人格化为例,socialism,以及它所理解的的“社会”,实际上是历史上各种宗教(连同它们各自的“上帝”)所提出的对秩序的泛灵解释的最新形式。socialism往往反对宗教这一事实也很难削弱这一点。
socialist以为所有秩序都是设计的结果,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秩序也能够由某个更高明的头脑加以改善。从这一点上讲,在埃文斯-普瑞查德《原始宗教理论》一书中初步阐述过的权威人物发明各种泛灵论的过程中,socialism也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socialism对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持续影响在史学和人类学的描述性研究中也十分明显。布罗代尔就曾问道:“我们中的哪个不曾讲到过阶级斗争、生产方式、劳动力、剩余价值、相对贫困、实践、异化、基础结构、上层建筑、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原始积累、辩证法、无产阶级专政……”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谈话的基础并不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而是对所讲事实的后果或起因的解释或推理。我们也尤其应当把一件事归因于马克思,即“社会”代替了马克思实际谈论的国家或强制组织。这是一种迂回的说法,它使我们认为可以用比强制更为温文尔雅的手段去支配个人的行为。当然,作为本书主题一直在谈论的自发形成的扩展秩序,几乎不可能像“作用于”或“对待”一个民族或一国人口那样,“作用于”或“对待”具体的个人。此外,“国家”或更为正确的“政府”一词,在黑格尔之前一直是普通的(或较为明确的)英语词,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也直白而明确地包含权力的概念,而模糊的“社会”一词,却使他能够暗示社会的统治将确保某种自由。
所以,正像智慧常常隐藏在字里行间,谬误也是如此。那些我们如今知道其错误的天真解释,以及那些常常不被赏识,但产生了极大作用的建议,通过我们使用的语言流传下来并影响着我们的决定。与我们的讨论尤其有关的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即我们在谈到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不同方面时所采用的许多词,都带有早期社会的误导性含义。实际上,包含在我们语言中的许多词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果人们习惯于使用它们,就会得出一些对间题的冷静思考不可能得出的结论,即与科学论证相矛盾的结论。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写这本书时,我给自己下了一个自我否定的指令,决不用“社会”或“社会的”这样的词(尽管它们难免会不时出现在一些著作的标题和我所引用的别人的言论中,并且我有时也会让“社会科学”或“社会研究”这类说法继续存在)。尽管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用这些词,但是在这一章里,我希望通过讨论这些词以及其他有类似功能的词,来揭露隐藏在我们语言中的毒素,特别是隐藏在涉及人类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制度和结构的语言中的毒素。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汉语堂):哈耶克:语言不仅传播智慧,而且传播难以消除的愚昧